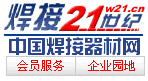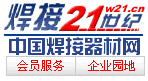曾经以为,我写下的文字是交给王侠的作业。渐渐发现有时确实有话想说。尽管我们的生活很世俗,平淡总被无奈惊扰,但总会有感动的时刻。在并不纯洁的心田里,也会有几朵鲜艳的花瓣。 曾经以为,我写下的文字是交给王侠的作业。渐渐发现有时确实有话想说。尽管我们的生活很世俗,平淡总被无奈惊扰,但总会有感动的时刻。在并不纯洁的心田里,也会有几朵鲜艳的花瓣。
(六)老歌
长沙是脚都,北京是首都。“中国洗脚之都”称号,娱乐城市长沙当之无愧。这个并非评比或竞争得来的称号,让敢为人先的长沙人民骄傲、气恼、无奈。 据说长沙有大大小小的洗脚营业网点数千家,说满街都是可能夸张了一点,但的确随处可见。服务质量也普遍不差。最可贵的是在长沙洗脚价格很便宜。除了洗脚,长沙还有更便宜的娱乐活动,那就是唱歌。便宜的让你感动——每人五块钱,管茶水,不限时间。
在北京,喝茶和唱歌都是比较奢侈的休闲娱乐,进KTV至少要花上几百元,茶馆的一壶水至少也要一百多。而长沙的音乐茶座,兼有茶馆和歌厅的双重功能,如果你手中还剩下十几块钱,基本就够请一次客了——仅限朋友,客户除外。
有个闲置的一楼的两居室,大点更好,又碰巧家中有个人下岗,开个音乐茶座就再就业了——配置一套音响,买几个桌子茶几,稍稍布置一下就可以营业了。捎带也卖香烟饮料。长沙娱乐的平民化、大众化,与其它某些城市相比有天壤之别。
上午九点就开门纳客。客人走进去,茶水是肯定有一杯的。唱不唱歌随便,不唱歌的就当去了茶馆。白天客人少,如果想唱歌,基本上就是专场音乐会。晚上或人多的时候,唱歌要排队,客人把歌名写在纸上交给老板或服务员就行了。客人们互动起来,气氛也很热烈。比较大的音乐茶座,也配有单间,价格贵了不少。
“老板,唱歌多少钱?”
“五块!”
——几年前我第一次进去,以为点一首歌五块钱。唱了十几首八九十年代的老歌,估计一天的差旅补助差不多没了。不敢再唱了。结账时,老板找了95元,吓我一跳。
“老板,没算错吧?”
“五块钱随便唱!”
“那我再唱一首吧。”于是我又学会了一首老歌《一条路》(张行、陈彼得),现在是我最喜欢听的老歌之一。它的歌词和旋律,总能带我回到从前。
如今,我仍经常有机会出差去长沙,却再也没有进过音乐茶座。有时在熟悉的门前驻足,想起曾经一起引吭高歌的五六个朋友。有当老板了,比业务员还累还忙;有娶妻生子了,每天早请示晚汇报;有快结婚了,忙着孝敬丈母娘;能歌善舞的美女,也不知嫁到哪里去了……
祝福他们走好自己的一条路,一路平安。
(七)奔丧
相信对任何人来说,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。
一生总会有大大小小千百种遗憾。有些遗憾会随着时间流逝逐渐释怀,剩下的少数遗憾可以称为终生遗憾。
对于子女来说,恐怕没有比母亲去世更悲痛的事情,即使你曾经不是一个孝子。母亲去世总会留给子女无尽的遗憾。因为人只能死一次,无法事先彩排。我正被深深的遗憾敲击。
今年的十月,我一直在出差,就在离老家很近的武汉。通常只要到了武汉,我总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母亲,哪怕只是寥寥几句。然而,十月的我,忙于所谓的业务,没有从百忙中抽出哪怕一分钟时间,拨通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号码。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。于是我的终身遗憾开始了。就在那一天的前夜,我居然还去了离母亲更远的黄石。不知道为什么,整整一夜都没有睡着。中午十二点,我正在邀请客户吃饭—点完菜但还没上,接到了最熟悉的电话—是父亲的声音,不详的预感突然冒了出来。果然,69岁的母亲脑溢血复发,已经不省人事,正要送到医院急救,父亲要我赶紧回家。这顿饭匆匆吃完,立即返回。二点钟,那个电话又来了—我知道,我失去了见活着的母亲最后一眼的机会。
到武汉已经是下午四点。我在车上已经通知了在外的两个哥哥,他们当晚乘火车或飞机从不同的地点到达武汉。我决定等人聚齐了一起回去。天空一片漆黑,细雨纷飞,汽车只能小心行驶。一百三十公里的路走了四个小时。当我们跪在母亲身边,已是凌晨三点。母亲静静地躺着,神态安详,仿佛活着。我竟然没有哭,连眼泪也没有。
连续三四天,忙于办理丧事。白天,还有接不完的业务电话,来者不拒。只有下半夜才能抽出时间陪伴冰冷的殡箱,守望镜框里的遗像。
乡邻都说:多好啊,有福之人,既没有拖累子女,自己也没有受苦。
那几天,无论是打麻将还是玩扑克,我们兄弟几个都只赢不输。牌桌上的亲戚们无奈地说:看来老太太对你们很满意,你们一直看护着长眠灯,焚香烧纸,孝心可嘉。所以她在暗中保佑你们赢钱。
我连续三天三夜几乎没有合眼,也不觉得疲惫。直到母亲的遗体被缓缓送入炉中,母亲的骨灰被埋进大地,才感到了巨大的失落和悲痛。那些天,像在做一个梦,随着锣鼓、秧歌、鞭炮、鼎沸的人声逐渐平息,梦醒了,永远失去了最亲的人。
丧事办完了。就要离开老家,各奔东西。一个堂叔问:你们做儿子的怎么都不哭?还不如儿媳妇们的表现……
我说:我不想当着很多人哭,我只想一个人偷偷地哭。
在酒店的房间里,我接到了一个老朋友的短信:子欲孝而亲不在,感同身受,终生遗憾。读罢短短两行字,悲从中来,眼泪刹那间成了决堤的海。
待续
2008-12-27
|
|